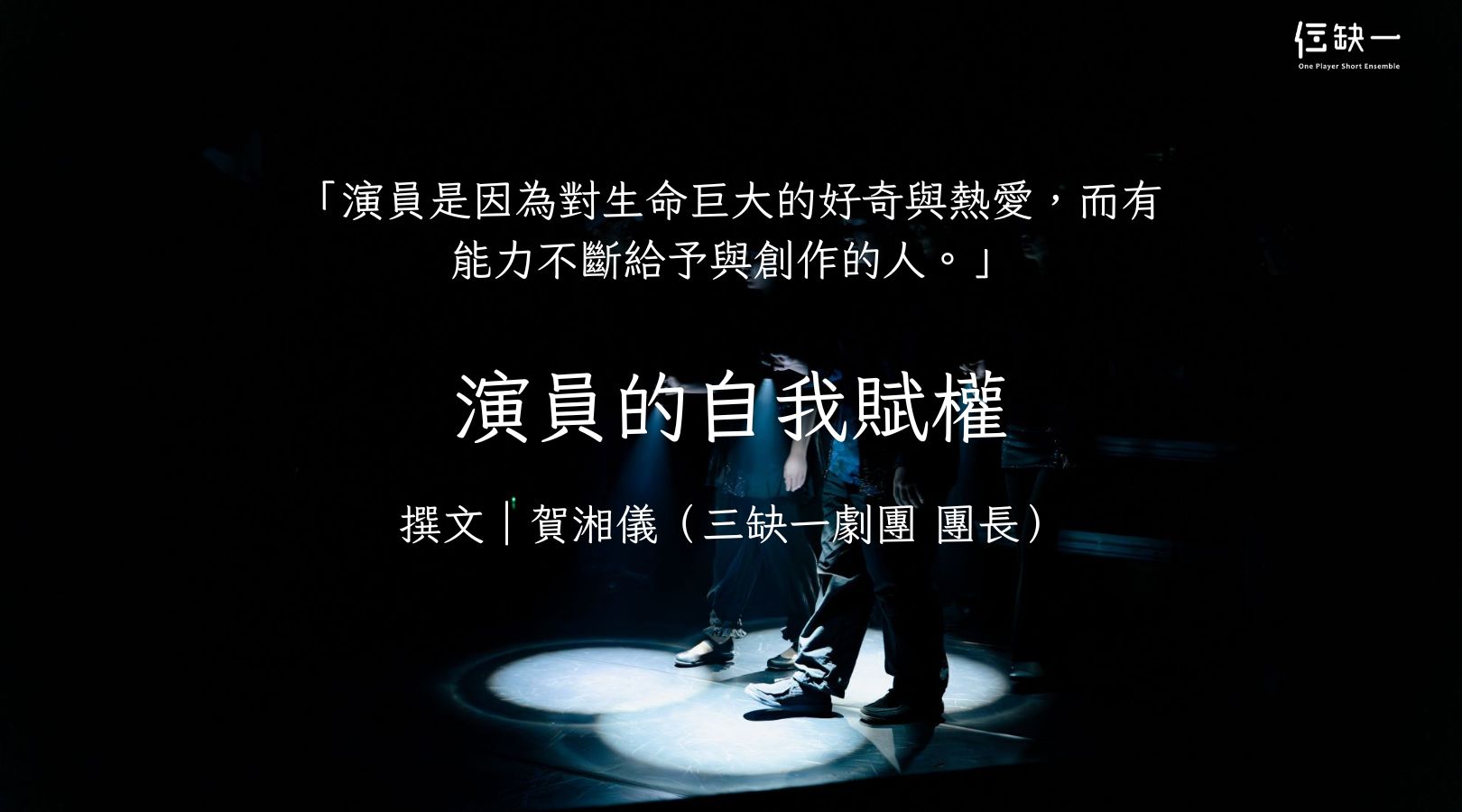撰文|賀湘儀(三缺一劇團 團長)
編輯|蔡茵茵
初嚐演員的滋味
我清楚記得我愛上表演的那一刻。那是2003年的初春,18歲的我在懵懵懂懂的狀態下成為了雋展的演員,我們幾個人蜷曲在輔仁大學旁邊巷弄中的學生套房裡排戲,在我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排戲的年紀。那個下午我們四個人排練了兩、三個小時,只排練一張A4大小,一場家人坐在客廳吃麵聊天的場景,很生活很日常的對話。我在那個下午愛上了表演。我第一次發現原來日常的對話中藏有那麼多的情感流動與潛意識,第一次發現原來人是如此複雜的生物,第一次發現原來表演可以帶領我去向生命的深處。
然而,我愛上表演之後,卻開始為表演吃苦,或者應該說,為了想「當一個演員」吃了不少苦;二十年後的今天,我成為一個劇團的團長,當了很多年的表演老師,遇見更多更多為了想當演員而受苦的人們。我常常會想,如果痛苦大於快樂的話,為什麼還那麼想要表演呢?
等著被評價的演員
表演最迷人也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拿自己當賭注。演員用肉身獻祭,將自己投擲於巨大的生命當中,放在他人眼前,震盪他人,搖晃自己。當完成使命,一種超越自身生命侷限的擴張感,好像擁有拓展生命邊界的超能力,叫人上癮;但是當任務失敗時,我們似乎也會失去原本自身的價值,肉身連帶著靈魂一同消失在他人的眼光之中。這種拿自己當籌碼的賭注,讓一個又一個的賭徒情不自禁地走向戰場。
但是,到底是誰來判定這場仗誰輸誰贏、成功失敗?以產業結構來說,演員看似光鮮亮麗,是最被觀眾認識的一群人,但其實根本就是在產業鏈下最末端的一環。在重重的考量與條件之下,演員是被選擇的,演員是被動的,演員永遠要把自己準備好,擁有十八般武藝與漂亮的履歷跟照片,然後,等待。等待錄取結果,等待觀眾反應,等待被宣判成功或失敗。
這是不是不太對勁?以自身作為賭注,卻只能等著被他人宣判,這怎麼看都太不划算。如果演員等同於把自己交給別人論斷輸贏與成敗,那注定只會是輸家。因為即便你獲得掌聲與認可,你就只能不斷去追求掌聲與認可。這大概就是為什麼《影后》這麼容易引起共鳴,為什麼演員應該可以被列為世上最容易迷失自我的職業之一的原因了吧。
守護身為演員的初衷
年輕的我卡在這裡,覺得自己不夠漂亮不夠主流不夠好也不夠有能力以演員維生時,我忘記我愛上表演的那個下午,我忘記是發現生命如此奧妙這件事引領我走上表演的道路;我忘記是對人的好奇讓我成為演員,而非為了得到他人的認可。直到2010年,我去到丹麥的歐丁劇團。歐丁劇團的演員們有一系列的單人表演,沒有劇本、沒有故事,內容就是演員示範他如何「研究表演」,做了哪些創作性練習。我還記得其中一位演員示範他研究日本的能劇如何使用聲音,然後他嘗試用那種聲音來說台詞。就這樣,不知道他練這個要幹嘛,但他只是在嘗試、在玩耍,在拓展自己覺得有趣的事,在真心享受。
我忽然被打醒,看見歐丁劇團的演員們出題給自己、當自己的老師,將自己視為表演的研究者與創造者,我看見的是他們賦予自己的權力:當自己的演員。演員如果是源自於對生命的好奇、探索、感動,而不得不將這些感動與發現分享給他人;那一個演員如果遺失了自己,又怎麼可能靠近他人呢?我終於看見,我在追求「演員」這個身分時,已快要遺失成為演員最根本的動能,我讓自己只是成為產業鏈中的一個螺絲,成為只是服務產業的人。

往後的十餘年,我走上自己的道路。從競爭激烈的女演員行列中出走,讓表演不再是我的唯一,開始教學、經營劇團、學習導演,更甚而開啟自己的副業。這麼多年下來,我的身分看似多重,也好像遠離演員的本業,但我知道我一直守護著身為演員的初衷——守護「我成為自己」的權力。包含日後成為劇團的經營者,我們也以培訓更多創作演員為宗旨,我們在日常的團訓中培養劇團共通的美學語彙,同時鼓勵演員們發展自己的創作。因為在台灣的教育體制、產業結構、文化脈絡之下,太少記得要去提醒,演員是因為對生命巨大的好奇與熱愛,而有能力不斷給予與創作的人。而如果他人忘記演員的權力與價值,就靠自己來守護。
演員的主動性練習
演員的自我賦權,對我來說正是守護演員核心價值的必要行動之一。但每個人到底要如何走出屬於自己的演員之路,卻又沒有標準答案可供參考,因為演員是關乎人的本質,無法被輕易分類,無法給予一本可被複製的成功指南,而必須透過自我不斷的探索與嘗試,逐步看見:我是誰?我想成為怎樣的演員?
權力真正的核心,是責任。我們有認識、看見自己的責任,然後才有能力自我賦權。因為知道自己真正要的是什麼,所以最終可以不被迷惑,也明白因此要付出什麼。正因為演員是產業鏈的最末端,被物品化的可能性很高,身為演員,更需要清楚的自我意識,才有可能找到不違背自己的生存方式。
這樣的結論聽起來很不負責任,因為我發現不論我如何舉例,都會有破綻,都會限制我們對於演員可能性的想像。可是,有一件事我或許是有把握的,那就是,不論你是在這個世界哪個角落哪種樣貌的演員,請記得,培養自己成為自己的導演,成為自己的表演老師。什麼地方做得好,什麼地方盡力了但不夠好,什麼地方偷懶了,你才是那個最清楚明白的人,不是導演、不是製片、也不是觀眾。你的分數由自己打,這是必要的技能。因此可以不要過分依賴他人,但同時要保有被鬆動的彈性;先去認識這個世界有多大,接觸各種表演系統與表演老師,找到自己所嚮往的與自己的根,然後行動,讓自己有能力前往所嚮往的世界。
這包含所有物質性的篩選,如何安排最適合自己的日常訓練菜單(而不是覺得自己什麼都不足什麼都想學)、如何建立自己的人脈網、如何規劃時間分配與短中長期的生涯想像。當我們每一步都走在看見自己的路上,知道自己在探索什麼,常常停下來辨別自己走在哪裡,為自己定錨後繼續前行,就好像航行在一望無際的海上,困惑有時,焦慮有時,但總是會找到方向。
我一直嚮往著繽紛、多元、充滿奇花異草,彼此不一定互相理解認同,但卻可以互相陪伴支持的世界。當我們更知道自己是誰,也就會更有空間允許他人也成為自己。所以我做的選擇,是我不只以單打獨鬥的方式行走江湖,而是透過經營劇團、教學品牌,與自己的副業來實踐我想要的世界。我喜歡看見劇團裡的演員們,可以一起玩耍、創作、爭論,一起在長大的過程中慢慢長成自己的樣子。讓自己成為自己,讓他人成為他,是我想繼續航行在這片海上的方向。
那你呢?

賀湘儀|作者介紹
三缺一劇團團長、演員、導演、表演老師、創作陪伴、芳療按摩師。曾參與再拒劇團、黑眼睛跨劇團、莎妹劇團、河床劇團、EX-亞洲劇團、無獨有偶工作室劇團、讀演劇人等劇團演出,表演經驗橫跨物件劇場、偶戲、肢體劇場、獨腳戲等。為三缺一劇團創始團員,並於 2017 年擔任團長至今。近年來關注透過身體來解鎖創傷,2024《陌生海》想進行一場眾人的感官之旅;《她們來聽我的演唱會》想為性創傷者而唱。
仨加一教室開課中!
2025 Summer 夏季班:「動物轉化創作工作坊 演員進階班 」、「給所有人的表演課」、「觸碰香香的身體」、「大叔的當代武術生存指南」、「林克雷特聲音訓練系統 Voice3、Voice4、Sound and Movement 」
課程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sfg5ocb9XzjWDv1u7
相關文章:寫實表演不是唯一,攤開一張表演地圖|魏雋展 – 三缺一劇團聊表演
相關課程:「仨加一教室」三缺一教學計劃,邀請你一起加入對表演、創作的探索與研究,讓我們充滿好奇,不安於室
相關影片
【關於我們】
三缺一劇團信箱:oneplayershortensemble@gmail.com
仨加一教室信箱:omp.workshop@gmail.com
三缺一劇團 官網:https://oneplayershort.com/
【社群媒體】
三缺一劇團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OnePlayerShort
三缺一劇團 Instagram:https://www.instagram.com/oneplayershortensemble/
三缺一劇團 Youtube:https://www.youtube.com/@oneplayershortensemble
-----
三缺一劇團成立於2003年,擅長以魔幻的手法,穿梭在寫實與寫意之間。
透過身體、物件與偶戲的多重變形,去撞擊出強烈的時刻。
取材於日常生活,引發自我與社會性的辯證。自2012年以來建立劇團兩大創作方向:
「土地計畫」:靈感來自於鄉野奇譚或口述歷史,透過田野調查,把生活議題轉化為故事劇場。
「LAB計畫」:演員的身體研發中心,回到古典三位一體的思維來重新探索當代演員的身體性。